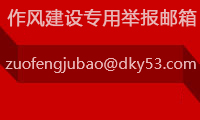跟著將軍去踏勘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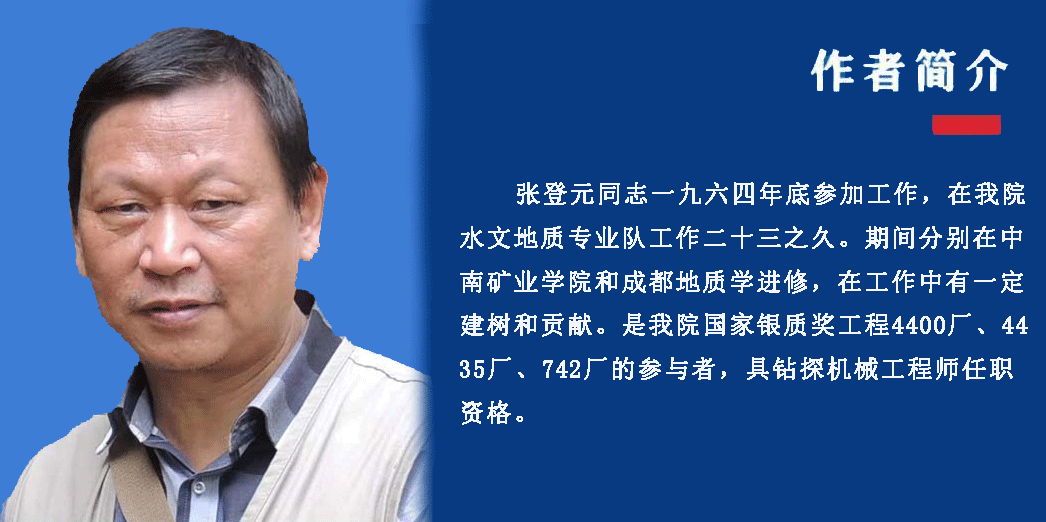
將軍說的是王宗金少將。
王宗金是貴州省習水縣隆興鎮新光村生基坳人,生于1916年。1935年1月參加紅軍,1936年入團,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。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,王宗金參加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,參加過桐梓、遵義、直羅鎮、東渡黃河等歷次戰斗。抗日戰爭時期,他曾任晉西區黨委、晉綏分局電臺隊長等職。解放后,被授予少將軍銜,任炮校校長,第四機械工業部副部長。他將畢生精力獻給了我軍無線電通信事業和我國電子工業的建設,并做出了顯著成績。從六十年代起,他負責基建工作,歷時20余年。從選廠、勘測、審查設計、開工建設到竣工驗收,他不畏艱辛險阻,忘我工作,無私奉獻,走遍了祖國各地。組織基建戰線的干部職工,建設了數以百計的電子工廠、研究所和院校,從而奠定了電子工業發展的基礎和三線后方基地。為電子工業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。1965年王宗金任四機部駐貴州基地辦事處負責人。負責組織都勻、凱里地區0八三基地建設指揮部,帶領所屬人員邊基建、邊組織生產和科研試制,為電子軍工基地建設做了大量工作。(此段內容為綜合網絡資料所得)
1965年正是我參加工作的第二年,這一年我隨隊到了貴州。將軍時任四機部基建局局長,親自抓0八三基地指揮部的工作。最初基地執行勘探任務的只有我們這一個隊,將軍常來看望我們。將軍衣著很簡樸,非常平易近人,完全沒有高級干部的架子。知道將軍是老紅軍,大家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。
和將軍最長的一次近距離接觸大約在一九七零年的夏天。那年我們隊在黔南執行306(信箱4506廠)的勘探任務,那個地方地質條件很復雜,無法解決地下水資源,將軍得知情況后再次來到我們隊指導工作。
將軍只帶了一位工作人員,這個人是從北京來的,一直跟隨將軍身邊。此人真的是‘人高馬大’,一米九幾的個頭,穿45碼的鞋子。將軍在聽取了隊領導的匯報后,決定親自去進行一次踏勘。隊上派地質工程師老趙和我隨將軍同去。第二天天剛亮我們就和將軍一起出發了。先由隊上的解放牌大卡車送了我們一程,之后沒有了公路,只能徒步。出發的時候隊上為我們準備了干糧,每人兩個饅頭、兩只雞蛋,各自再背了一軍用水壺水。那天將軍頭戴一頂麥秸編的草帽,腳上穿了雙布鞋。我知道這天要走長路,沒有穿翻毛牛皮鞋,特意穿了一雙高腰解放鞋。就這樣我們一行四人在將軍的帶領下,向山間走去。踏勘工作走的都是不熟悉的地方,全靠一張五萬分之一軍用地圖指引。踏勘都踏什么?當然是尋找適合建廠的地方,首先要符合三線建設靠山分散隱蔽的要求,這個條件在貴州高原倒比較容易滿足。關鍵是還要綜合考慮水、電、路等后續建設的條件。
在行走的路上我好奇地問起了將軍當年參加紅軍的情況。將軍倒也很爽快,滿足了我這個年輕的勘探隊員的好奇心。將軍是在遵義會議后參加紅軍的,當時他們的村子里駐扎著紅軍的隊伍。受紅軍革命宣傳的影響,村子里很多的貧苦農民都參加了紅軍,將軍和他的父親一起參加了紅軍的隊伍。當紅軍到達雪山的時候,很多剛參加革命隊伍不久的農民打了退堂鼓,跑回家去了,將軍的父親也回去了。但是將軍堅定的跟著紅軍隊伍走了,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,成長為共和國的一代將軍,成為新中國電子工業的奠基人之一。
這一天踏勘所走過的路,從地圖上看來回步行的距離也就七、八十來里地。同行的四人中我最年輕,還就數我不行,天生平腳板走不了長路,往回走的時候到后來都一瘸一拐的了。那時將軍都五十多歲了,一路走來毫不顯疲倦,依然精神抖擻。
這次和將軍分別之后再也沒有見到過將軍,但他一直在關心領導著我們的工作。改革開放之后,在文革中因為‘蝸牛事件’而停下來的彩色顯像管廠引進建設項目,重新提上議事日程。初步完成選址工作之后,由于彩色管生產用水量大,最后的拍板還要等待水文勘探結果。七八年的隆冬執行水文勘探任務的我們奮戰在第一線,在克服了技術、設備等等的困難之后,于某天午夜過后取得了揚水實驗的成功。一直在施工現場的革委會王副主任(解放戰爭時期入伍的老革命)立即將此喜訊上報北京。而此時在北京等候消息的正是將軍,原來在此期間已擔任四機部副部長的將軍一直守候在北京的辦公室,等待著我們的勘探結果,由此拉開了我國的第一座彩色顯像管廠的建設序幕。
現在將軍雖然已經遠去,但將軍忘我的工作精神、平易近人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,將軍的音容笑貌卻永遠留在我的心中。
2012-07-06